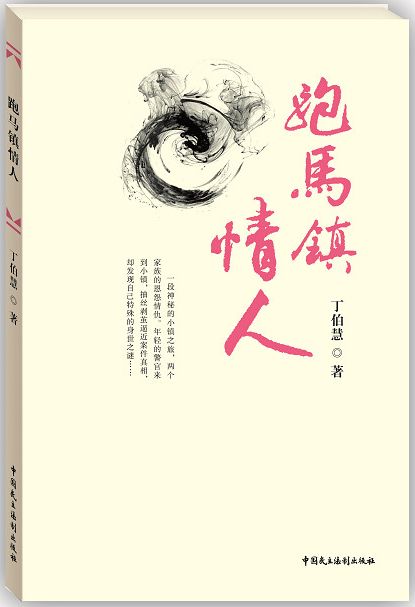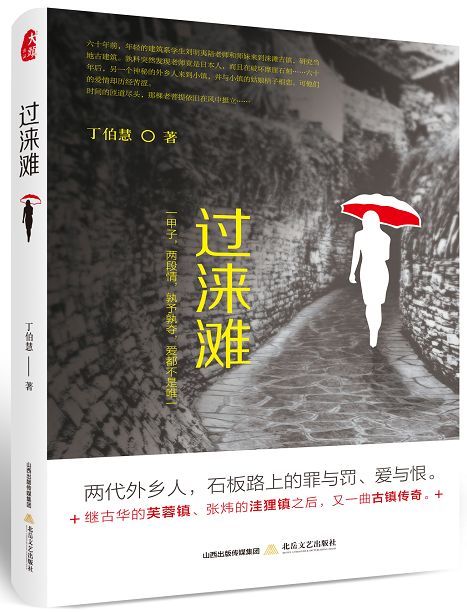两江夜雨丨重庆作家 本期人物 |
您所在的位置:网站首页 › 丁文章 重庆两江 › 两江夜雨丨重庆作家 本期人物 |
两江夜雨丨重庆作家 本期人物
|
(2009年5月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) 长篇小说《草木皆兵》 (2010年1月,湖南人民出版社) 历史散文集《微历史:民国就是这么有趣》 (合著,第一作者)(2012年3月,江苏文艺出版社) 长篇小说《跑马镇情人》 (2012年6月,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)
长篇小说《松林一号》 (2013年2月一版,2016年1月再版,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) 专著《创意写作》(合著,第一作者) (2016年9月,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) 长篇小说《过涞滩》 (2017年1月,北岳文艺出版社)
长篇小说《第三只手》 (2018年8月,明天出版社)
主要获奖 长篇小说《跑马镇情人》 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大赛长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《归去来》 第七届重庆文学奖 、首届湖北新屈原文学奖 各方评论 郑 润 良 青年文学评论家,副教授,厦门大学博士后 不管是对小镇,还是大海,丁伯慧其实都寄寓了自己的某种理想化的向往与吁求;小镇与大海,与其说是他曾经的经验之地,不如说是他想象中的飞地,使他在这个喧嚣、热闹、功利化的世俗世界中时时回味与向往一块想象中的静土。可是这样一个宁静安详的世界,究竟是不可再得的吧。在这个躁动、迁徙的时代,如何去寻找这样一块安身立命的乌托邦呢?也许,丁伯慧自己也知道这更多的是一种奢望,所以他只好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迁移、流浪、纠结,也不断地探询、思虑、摸索。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吧。 张 执 浩 著名诗人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,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他在与生活互动,而一个写作者只有在作出了将自己全盘托付给生活的决定后,他才敢于去承受迎面扑来的粉尘和烟雾。丁伯慧显然已经具备了这种承担的勇气和能力,即,爱与恨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不是作家在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后所能“体验”到的,而是置身其中以后所产生那种古老的情怀:道义,良知和悲悯,等等。这样的情怀实际上早早地就潜伏在我们个人的体内,但由于外在生活的不断侵蚀和打磨,使我们麻木了,遗忘了。现在,我们得弯下腰来,蹲进自己的体内,在黑暗中寻找和挖掘它们。 因此,我要向丁伯慧表达我的谢意,阅读他的小说使我感到了快乐。 陈 宗 俊 文学理论家,南京师范大学博士,安庆师范学院教授 在当代中国70后作家中,丁伯慧也许不是最优秀的,但却是较特殊的一位。这位生于皖山皖水间、现客居于重庆的青年作家,有着同龄人少有的人生阅历:种过地,当过海员,做企业管理,主编过刊物,还客串过心理咨询师。这种较丰富的人生足迹,与大部分“还没有站起来就趴下”的70后作家相比相距甚远。丁伯慧的作品,记录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思考、对生命的聆听与感悟,朴实中不乏细腻、粗粝中显现知性,就像一位多情水手的歌哨,在大海与苍穹之间低回。 作家在《小说到底写什么》一文中指出的:“小说写的,其实不是别的,只是小说家的良心。”这是一个沉重的字眼。这种良知来自于作家心底的自觉,就像出身于卑微农家的作家本人,对人世总存一份悲悯和关切,所以丁伯慧的文字在热闹的背后显示出一份厚重与悲怆,这也使得他的写作获得了与同龄人作品少见的强度与力量。 作品选录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。年前刚刚下了一场大雪,整个村子都被雪裹住了,屋檐上还结了冰溜,一条条的,长短不一,形状各异,像一把把刀子悬在头顶。雪化后,刺槐还是光秃秃冷冰冰的,孤零零地,在寒风里立着。几只乌鸦在村头最高的那棵大枫树上高声叫着。这样的天气适合做丧事。 大伯躺在棺材里,脸上作了处理,有了些血色。他身子下面垫着白棉布,周围铺满了石灰,脸上很平静,好像他这辈子过得很平静一样。几天前照全家福的时候,他大概不会想到,他的一辈子,就这么过完了。听堂弟来富说,昨天晚上喝了几杯酒,他们睡新楼房,大伯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,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叫他吃饭,没人应,撬开门后发现,大伯一个人躺在地上,身子已经硬了。后来村里的医生来了,说应该是心肌梗塞,难受,叫人没人应,疼得从床上滚到了地上。 来富哭着说,都是新房子啊…… 他哭得很真实。 就在这几年里,农村里突然兴起了楼房。所有人家,不管有钱没钱,只要想娶媳妇,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楼房。有钱的人家做三层四层,大红瓦,飞檐,大院子,院墙又高又厚,上面还扎满碎玻璃。没钱的人家就竖两层小楼,屋顶上是平层,正好晒稻谷,屋里就用石灰简简单单地刷一下,亮得晃眼。那几年里,大伯的唯一心思就是给来富娶媳妇。来富读完初中就跟人学手艺了,学的木工,出师后就自己出去打工挣钱。这时年轻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了潮流,大伯也不说什么了。出去两年,年龄也差不多了,到了该找对象的时候了。托了很多媒人,四处打听,都摇头。这些年里农村的姑娘本来就越来越少。一部分考上了大学进了城,变成了城里人的媳妇。一部分出去打工嫁给了城里人,还是城里人的媳妇。剩下的姑娘就跟宝贝一样,一过十八就有很多人家上门抢了。 媒人说,第一,你们家没有楼房;第二,没有婆婆。难啊。关于第二条,媒人解释说,来富一年到头在外打工,屋里头就剩下年轻的公公和儿媳妇,别人要说闲话的啊。 很多人劝他赶紧给来富找个后妈。做牛贩子的根苗还托人给他找了一个。女人四十二岁,看上去像五十八,有些虚胖,黑黑的,走路一摇一摆的,像只鸭子。根苗跟大伯解释说,这个年纪,就是找个伴嘛……大伯直摇头,说长得太老了,看上去可以做来富奶奶了。好说歹说,大伯勉强同意了。但是那个女的屋前屋后转了几圈,斜着眼睛说,整个家里,就屋前的杉树值几个钱,还得几年长。苗竹不值什么钱。那片桃树林卖桃子,一年撑死了五百块钱。 死活不同意。根苗鼓动他那张牛贩子的嘴,那女人最后才松了口,丢下一句话,做楼房,做了楼房就来。大伯对着她肥胖的背影啐了一口,有楼房我要你啊,呸!后来又黄了几个,都是因为大伯不同意,这事才算是彻底搁浅了。 节选自短篇小说《如果有风吹过》 面 对 面 重庆晚报:您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,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雄心,那就是让自己的作品留下来,成为经典。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? 关于经典,耶鲁大学的教授哈罗德·布鲁姆是这样说的:“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,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,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。”可见,成为经典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你必须在前人的基础有自己的创见,并且能够给后人以启发。换言之,你的作品里必须有一直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。当然,对于经典,布鲁姆更多的强调它的“陌生性”。事实上,每个作家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这种“陌生性”。这种“陌生性”既有“写什么”上的独特发现,也有“怎么写”上的独特创造。 重庆晚报:青年评论家郑润良博士认为,“历史书写向来被认为是70后作家写作的弱项,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某种共识。”他在评论中提到,“《过涞滩》历史意味浑厚”。作为70后的你,为何迎难而上,创作了《过涞滩》这部书写小镇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? 历史与文学,从来都是很难分割的一对兄弟。一方面,西班牙人有谚:“小说被称作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另一方面,历史学家克罗齐说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古往今来,“史诗性”一直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之一。小说们企图用文学来书写另外一种被遮蔽的历史。当然,历史性的书写是艰难的,但是涞滩古镇值得这样去书写。我第一次去涞滩的时候就被她吸引了,感觉这地方有一种能够进入我灵魂深处的东西。 重庆晚报:我们知道,您是一个工科生,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?支撑您写作的主要理由是什么? 时常有人问我,你一个学工科的,做海员做得好好的,干吗要来写作?我的回答是:写作可以让我选择不同的存在方式。 的确,每个人,都只能活一辈子,在他的人生中都只能以一种方式来存在。但写作的人,尤其是写小说的人不是,他可以生活好多辈子。这是很多不写作的人所不能明白的。当然,这里面首先得弄清一个问题:你是在以哪种方式写作? 我认为,小说家的创作方式通常有两种,一种是导演式,一种是演员式。前者以为自己是可以纵横捭阖的指挥者,指挥着小说中的人物干这干那,甚至把生活中自己想干却干不了的事情也在小说中干了;而后者则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,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,一起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,而他只是一个记录者。 坦白地说,我比较赞赏后一种。姑且不论对错,就我而言,之所以愿意选择这种方式,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多活几辈子。 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,我的参与都是深入的,有时候甚至回到生活中还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。这种深度参与是痛苦的,也是幸福的。痛苦的是,你必须去更多的担当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只要成为小说中的人物,没有一个日子是安逸的,他肯定要经历很多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。幸福的是,你可以让自己从庸常生活中暂时地剥离开来,暂时地忘记真实生活。写作,其实也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。 重庆晚报记者 罗雨欣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 |
【本文地址】
今日新闻 |
推荐新闻 |